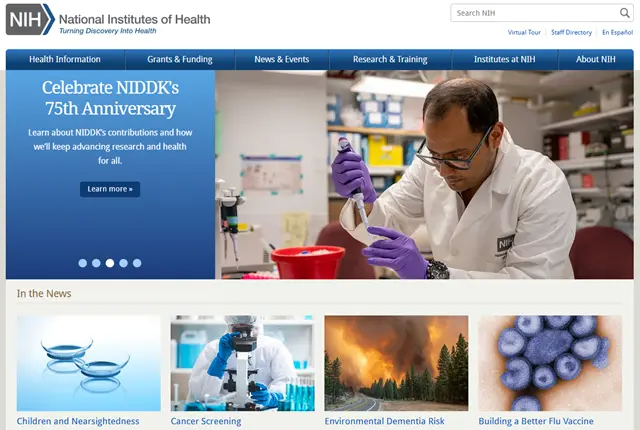1962年以前,《國防教育法》資金的受助者必須簽署一份宣誓書,聲明自己不支持任何試圖推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然而國會中的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擔心部分資金可能被用於推動廢除種族隔離,於是添加了一項條款,規定該法案的任何內容都不得允許聯邦政府支配學校的課程、教學、管理或人事安排,這是由錯誤動機促成正確政策抉擇的典型時刻之一。
這部法案還通過向有需要的申請者提供低息貸款,在推動全國高校多元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客觀上挑戰了限制猶太裔、亞裔、黑人、波蘭裔及義大利裔等弱勢群體入學的政策。上世紀60年代初,在我本科就讀到一半時,耶魯大學迎來新任校長,迅速推行多項改革措施,包括破除舊有的排猶風氣,並錄取更多以往可能僅僅因為姓氏而被拒之門外的學生。
這些轉變最終對我的職業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回到耶魯讀研時,《國防教育法》資助我拿到博士學位。並非政府將莎學研究與火箭科學混為一談,而是這部法案的第四章要求擴大大學教授的規模,將資助範圍延伸至人文與科學雙重領域。斯普特尼克衛星的發射最終也把我納入了它的軌道。
這項始於國家安全的計劃最終化作激發無限好奇心、創造力與批判思維的引擎。在美國大學的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支持下,發明與創新源源不絕地湧現出來:互聯網、核磁共振成像、DNA重組、人類胚胎幹細胞、CRISPR基因編輯,以及使得mRNA技術得以成型的眾多研究成果(mRNA 技術為包括新冠疫苗在內的新一代疫苗誕生打下了基礎),不一而足;同時,我們對物質及宇宙起源的認識也取得了劃時代的突破。
巨額稅收的注入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不僅培養了科學家、醫學研究人員和武器工程師,還孕育了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美國大學的獨特結構打破了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與其他學術領域的壁壘,無論是在本科課程體系中(學生幾乎必須完成通識教育),還是在校園文化中。
傳統的研究邊界開始瓦解。1969年我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此執教數十年裡,經歷了一些振奮人心的年代。一位富有遠見的院長曾分發問卷,詢問理工科教師最常與哪些學科同仁探討研究工作。根據收到了反饋,院系進行了重組。創新活力隨之迸發。理工科院系辦公樓外的停車場設立了多個「諾獎得主」專用車位。
到1990年代,美國大學已成為全球文化的標竿——其學術廣度令人艷羨,學術自由備受推崇,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將其視為自由探索與學術威望的頂峰而趨之若鶩。政府雖未刻意創建自治的國際化知識殿堂,但其投資規模——以及大學相對遠離直接政治幹預的特性——促成了美國大學發展為至高的文明成就。